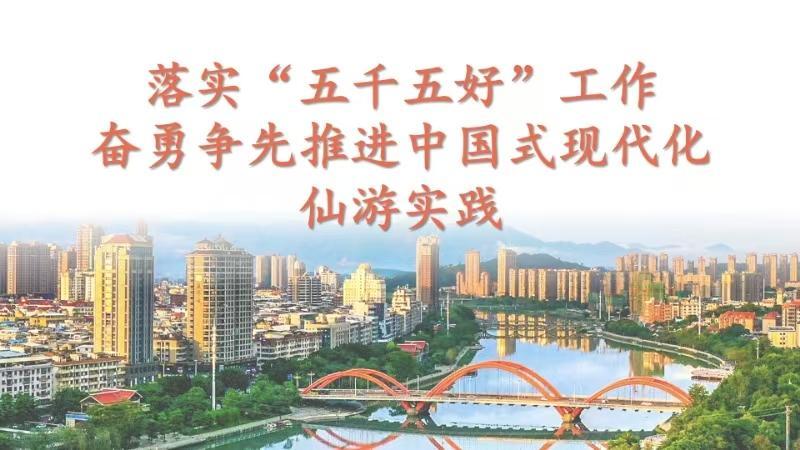在春天,抵達木蘭溪源頭
仙游山因木蘭溪源頭而聞名,來仙游山,一定要去木蘭溪源頭,這是一個與所有莆仙人都有淵源的地方。 木蘭溪源頭位于海拔869.74米的仙西村黃坑頭,是仙游山的核心和靈魂。愈靠近源頭,愈發意識到我這是去探訪一條與我息息相關的河流的源頭,由此,愈發為自己太遲來這兒而心生不安。 一路沿著齊整的水泥路駛過仙山村,又是一個岔路口,一頭往仙獅祖殿,一頭往仙西村。我們在路標指示下,穿過仙西村,抵達村外荒野里的源頭入口處。 過了入口處的“思源亭”和“抱芋上書”石,拐上一條泥土小徑,再往里走一小段,在一泓碧水旁的“木蘭溪源”景觀石下,我們遇到十來位仙游一中的老師。這里環境清幽,一邊是瀲滟的碧水,一邊是綠意婆娑的林木,正好可以讓人在此好整以暇一番。此時陽光明媚,粼粼的水面上像鋪了無數的碎鉆,白亮晃眼。經水面衍射后的陽光漏進砸地的樹蔭里,灑下的碎影在這些優秀教師的身上跳躍著,使他們顯得神采奕奕。湊巧的是這一群人中有好幾個我認識的朋友,看到我,他們也很驚訝。一問才知道他們今天是來開展黨建活動的,正要去源頭,于是加入他們的隊伍,一同前往。 循著谷澗邊的一條小徑走了一會兒,過“清源亭”,再走一小段路,木蘭溪的初始原貌便以山野間的一泓泉水之姿呈現在我們眼前,雖有點驚訝,卻也在情理之中。一條河流的初始面貌,就應是如此,藏于深山中,清且漣漪,純粹、自然、守拙。盡管此源頭難以讓人與那條流淌在閩中大地上的恢宏河流對上號,但它是無窮無盡的陸離斑駁的鏡像之源,是孕育閩中大地一切傳奇和無限可能的濫觴。木蘭溪就是從這兒出發,一路上穿山越嶺,沿途匯集涓涓細流,歡騰地穿過西鄉東鄉,坼分南北洋,最后在興化灣匯入大海。 仙游山人十分珍愛源頭,用石塊圍砌成一個泉池,并用竹子引流,供人取用留念。仙西村黨支部還給每個人準備了一個定制的小瓶子,眾人排著隊依次用瓶子盛滿源頭的水,鄭重其事,很有儀式感。瓶子里的水純凈清冽,盈盈地握在手里,清涼沁人心脾,有一種融入春光里的舒坦。 河流的源頭總是把人引向遠方。暮春時節,承蒙時光不棄,我們來到仙游山,“草木蔓發,春山可望”,“步仄徑,臨清流也”,突然有了遐思的時空,便“寂然凝慮,思接千載”。在閩中大地上,木蘭溪干支流如根系般蔓延著,像一條溯源生命的通道。透過這條通道,我們這些自稱木蘭溪兒女的人往溯自身的血脈時,一定可以穿越邈遠的時空,回到那條橫貫北方中原的偉大河流邊上。推本溯源,位于黃河中下流的中原地帶是莆仙先民最早的棲居地,我們這些后人的身上自然也流淌著黃河文明的因子。時至今日,莆仙人的方言習俗都帶著古中原河洛文化的印跡,這些如同生命中運行的密碼一般,一旦對上號,就能一下子校正方向,指向北方中原這個精神層面上的原鄉。 溯源莆仙人的遷徙史,大規模的移民潮起始于兩晉交替時的“文冠南渡”,再由唐中晚期延續到五代十國時王審知入閩,其后還有兩宋之交的移民潮,大都由中原一路向南遷入閩中。先民們毀家紓難,孤注一擲,“泛若不系之舟”,在阡陌縱橫的大地上轉徙,跨越過一條條河流,最終落腳在木蘭溪畔,繼續在閩中大地上深耕著來自黃河流域的中原文明,再造一個“海濱鄒魯”,于是在閩中大地上有了“莆仙人”這一新的群體。 在這樣一個陽光流淌的春天里,風和日麗,山川俊美,我穿過莽原,踟躕于春色盎然的山野里,被一泓清泉所釋放出的情思纏繞著、慰藉著,催生出一種溯源生命的意識,理清了“從哪里來”的問題,而后“要往哪里去”這個避不開的問題又上了心頭。 活了大半輩子,我不清楚經歷了怎樣的迂回之后,才遲遲地抵達閩中大地這一方水土的原鄉,但我知道如果順著源頭一直往回走下去,在經歷曲折迂回之后,一定會走到中游一個叫鯉城的地方。我土生土長在那兒,與這條河流朝夕相處,卻往往視而不見,其結果就是讓人在庸碌的生活中失去了方向感,而在仙游山,源頭仿佛是一個清晰的坐標,讓人消除了初來乍到的陌生感,也不再迷茫。在源頭的所見所思如一個參照體系,幫助我梳理了很多事,讓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聯。 仙游一中黨支部一群人還要趕別的行程,我和朋友則在源頭多待一會兒,讓思緒繼續流淌。 暮春的山野,絢爛和煦,當我的思緒隨著泉源流淌在春光里的時候,穿梭于林間的風搖曳著剛泛出新葉的繁枝,和著淙淙的泉流聲,仿佛奏響了一首舒緩而又遼遠的歌,牽引著我,一路流淌下來,流經過去、現在和未來,依然澄澈無垢…… |